
著名的古植物学家和孢粉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徐仁教授是我的导师,于1992年不幸病故。先生逝世,我深感悲痛,谨以此文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

先生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十几年来,我受先生的教诲,终生难忘。他不仅教我如何做学问,而且教我如何做人。
1978年,当我报考徐仁教授的研究生时,大有自不量力之嫌,加之我以前与先生从不相识。初试完毕,先生阅卷后很高兴,并约我到他家里谈话。在书房里初次见面,先生十分和蔼可亲。他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一边谈他的想法。因为我的各科考分都在80分以上,先生认为,从植物系统学的考卷上看,我的思路清晰。他特别强调,在科学研究中,思路清晰非常重要。只有紧紧抓住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努力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先生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座右铭。
先生建议我改变原报考的研究方向,由研究新生代植物转到研究陆地植物起源和早期演化。他认为,这样的改变对我来讲是扬长避短。他特别告诫我,这项研究难度很大,但是非常重要,是本学科的前沿课题。只要做出成绩来,就一定具有国际意义。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
我跟随先生十四年,在早期阶段,因先生要指导四名研究生,又领导一个研究室的工作,加上他自己的研究课题,工作很忙。我与先生接触的机会甚少,他对于我的学习,主要是指明整个研究工作的方向,其余一切则放手让我自己去干。直到毕业论文完成后,请先生过目时,才有了一次较为深人的谈话。他一再强调一个学者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非常重要。一位新人出现在某一个研究领域,他的第一篇文章往往会引起同行的重视。如果这篇文章水平高,以后,同行们就会注意他的每一篇文章。相反,不注重质量,随随便便发表文章,只会对自己有害。几年之后,我就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题征求先生的看法。先生一贯重视文章的质量,认为一篇好的科学论文会长久的被后人引用。如果只着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文章发表的快,发表的多,被人遗忘的也快,也多。
1981年底,我获硕士学位后,先生执意要留我在植物所工作。一年后,同时留所的大师兄去了美国。当时,先生也曾极力推荐我去美国.但是,先生考虑到自己年势已高。很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鉴于此情况,我向先生提出可否跟先生在国内读博士。先生欣然答应,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要求我读在职博士。问其原因,原来先生看我读硕士时,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因为不是在职,没有奖金。夫妻二人带一个孩子,每月有限的收人,生活倍觉艰辛。因此先生坚持我必须读在职博士,这样每月还可以得到几元钱的奖金。先生爱惜学生之情深深感动了我`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我再次成为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植物所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由此开始,我与先生的接触日渐其多。
这个时期,他已患有眼疾,大部分时间在家从事研究工作,我时常去先生家汇报工作或征求先生的指导。先生喜欢与我长谈,往往是从早上谈到日落。从他的身世谈到学业,从学业谈到事业,从事业谈到他的为人,从为人谈到人际关系,从培养学生谈到科研体制,从自然科学谈到辩证法。先生知识面广,思路敏捷,分析精辟,语言亲切。有时先生谈我记录,有时边谈边讨论。不知不觉,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思想、方法和做人的准则。

徐仁先生1910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29年考进清华大学,当时因家境贫寒,为了找工作容易,学习物理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他酷爱大自然,决心改学生物,立志研究进化论。他在著名生物学家张景钺教授指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云南大学生物系等高校从事现代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的教学和研究。1943年,先生作为客座教授应邀去印度,从师于世界著名古植物学家萨尼教授,鉴于工作出色,勒克瑙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此期间访间了瑞典的哈利教授和英国的哈里斯教授。1952年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的研究。这时,他已从事十四年的现代植物学的研究,因此,采用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化石植物,真可谓得心应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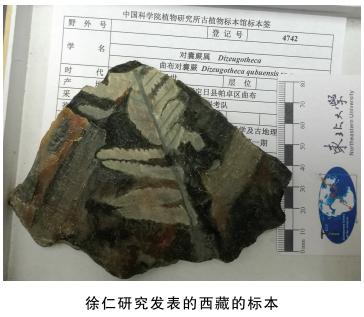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发表论文近60篇,主持和参与完成了6本专著,为古植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先生毕生追求真理,探索生物进化的规律。他对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允许保留和争论,但是绝不苟同。当有人提出混合植物群一说时,先生持有异意。他说,要从历史发展上,从动态上去观察和研究植物群的衍变,不能简单的认为某种现象的出现就是两个植物群的混合。一次当法国外宾在学术报告中谈到混合植物群时,先生当即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
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人际关系上,对于不同的意见,甚至发难之事,先生都能虚怀若谷,宽宏大量,主张让历史,让事实来证明是与非。先生平易近人,为人诚恳,对青年人关怀借至,从无一长者的傲慢。先生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其中不少年事已高。几乎所有的学生对先生的敬仰之情都深如东海。
在谈到培养研究生时,先生认为历来有两种方法。一是导师手把手的教。从选题,采集材料,实验设计,整理文献直到完成论文,均由导师从旁指导。如此教学,对于学生来讲,易学易做,进展快且顺利。另一种方法是导师仅仅指明研究的方向,思路和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以后任凭学生自己去摸索,去发挥。对于学生来讲,这样做学问的道路是很难的。不过,一旦闯过来了,对于今后独立开展研究工作是大有益处的。到了此时,我才明白,先生一直在采用后一种方法培养我们。我问先生为什么采用此法育人,先生答道,我的老师张景钺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先生曾指出,一个人做学问能否成功,第一重要的是勤奋。懒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先生寄希望他的学生能有所建树。他多次讲过,学生应该超过老师,青出子蓝而胜于蓝,否则,老师就不是高明的老师。对此,我也曾谈过我的看法,先生是三、四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全才,同时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就。就这一点来看,没有一个后人可以与先生相比。做为学生,也许在某一个方面多做些工作,取得多一些成绩是应该和有可能的。
先生对中国科学院与各大学分开的作法很不满意,认为不利于科研和教学的结合,不利于人才的挑选。他认为现行科研体制的最大弊病是人员不能流动。想要的人才进不来,想出去的人又走不了。对于恢复研究生制度,他认为是一个挑选和培养人才的好办法。
他多次鼓励我阅读有关辩证法的书籍。他自己常常是手不释卷。他说: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问题,就会走人迷途。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工作者应该经常从自己熟悉的微观领域里跳出来,看看植物学在宏观领域里的发展,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发展。
从硕士生学习开始,经过8年的努力,1986年我终于到了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按照先生的要求,我的博士论文以英文写成,并送给英国、美国、德国和我国古植物学界、植物学界的专家权威审查和评阅,所有专家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此,先生格外高兴。答辩前一天,遵照先生的嘱托,我专门去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部委员会主席汤佩松教授出席答辩会。刚刚病愈出院的汤先生高兴应允。答辩会上,一切顺利。汤先生,徐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都为我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
1987年,在先生推荐下,我获得了前联邦德国的洪堡奖学金,赴德国做博士后研究。出国前一天晚上,我去医院向住院治疗的先生辞行。先生嘱咐我,出国无外乎做两件事,一是看看人家的工作,了解人家的思想、思路和掌握本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二是广交朋友。夜深了,不得不与先生告别了。先生拉着我和我妻子的手,深情的对我妻子说,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全靠你的支持。
这一走就是三年。我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习和在英、比等国的访问学者的研究工作后,原准备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访问。但是,我得知先生重病在床,希望我尽早回国。1990年夏,我与妻子,女儿回到祖国,回到先生的身边。
先生已80高龄,久病卧床。见到先生,我和先生都流下了热泪。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跟我说,我有病在身,不可能再给你什么帮助了,以后的路,你自己去闯吧!当谈到我回国后没有研究经费等重重困难时,先生鼓励我想办法克服困难,为发展中国的古植物学而努力奋斗。当然,先生最后又说,如果你实在有困难干不下去的话,也只好再次出国吧!说到这里,先生的眼泪又一次涌出。我知道,先生心里难过。他渴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否则,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回国后不久,我得到中国科学院和植物所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及时帮助解决了各种困难,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开展起研究工作。对此,先生得知后特别欣慰。
在与先生相处的最后时期里,每次去看望先生,他总是询问研究室的情况,研究工作的进展。在我申请破格越级晋升研究员时,先生用颤抖的手为我写了推荐,并且连声说,应该上了,应该上了。在三位学部委员和两位教授推荐下,我通过了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的审查,晋升为研究员。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十多年努力的充分肯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先生培养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许。
先生已乘黄鹤去。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呈现在我眼前,他谆谆教导依旧响在我耳边。作为后人,我们将继续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努力工作,继往开来。
作者:李承森,原刊于《植物杂志》1993年第3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