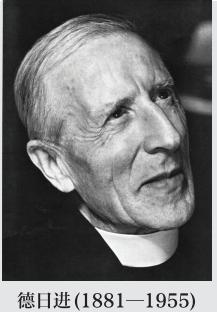
我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名练习生,于1931年春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大约是这一年的5月间,我和卞美年跟着裴文中先生一起来到了周口店。两、三天后,德日进、步达生和杨钟健三位新生代研究室领导人乘车也到周口店布置工作。这是我和德日进神父首次见面。当时我还年轻,只有23岁,又是个练习生,当然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多少话可说;但德日进神父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那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与和蔼可亲的谈话语调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他培养青年是不遗余力的。我们那时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周日店发掘,半年的时间在北京城里的研究室工作。一到北京,和德日进神父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大概是1931年冬天,我刚从周口店回到北京城不久,我和他都在西城丰盛胡同地质陈列馆的后楼上工作。他在里间研究周口店的石器(步日耶神父也在这里观察过石器和骨器),我在外间整理周口店的化石和编写石器号码。在我的面前放着一个很糟朽的鹿角,刚刚用胶粘好,他一看到就想用手拿它详细观察。我怕弄坏它,本来想说请他先别摸动,可是慌里慌张地想不出适当的英语字眼,竟然说出:“请举起手来”。他马上哈哈大笑起来,举起双手作投降的样子给我看,纠正了我的错误,告诉我如何说才对。此后,和他接触的机会愈来愈多了,他教给了我许多科学知识,也替他测量了不少标本,成了他的一名助手。
当他在新生代研究室担任顾问和特约研究员时,工作地点有四处:除了上述的陈列馆的后楼外,一处是西城兵马司胡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西楼,一处是东单三条胡同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科,还有一处是东单北大街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娄公楼。他经常在娄公楼106室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间,裴文中、卞美年、绘图员王松峪和我都曾在这一间工作室里工作过。他在这里研究过许多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为我们修改过许多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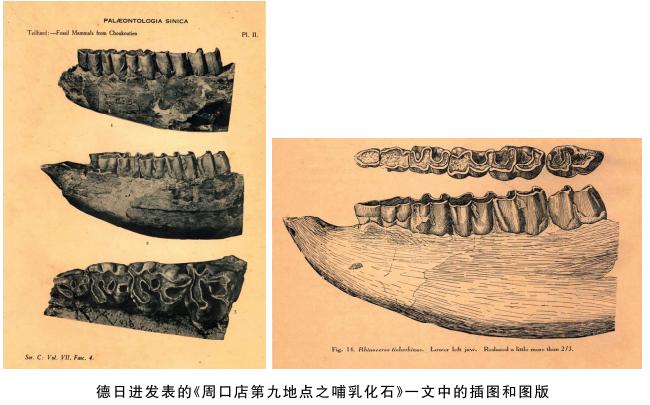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开始后,周口店的主要发掘虽然停止了,但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仍然勉强维持。他和杨钟健商量之后,把中央研究院交来的河南省濬县殷代遗址出土的马骨交给我来研究。嘱我辨认出匹数、年岁、性别以及是否有驴或骡等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为了更好地学习,还是把任务接受下来了。报告写完之后,交给了德日进神父,他改动了很多,用他那文雅而秀丽的字体,把我那大约二十页上下的英文稿逐字逐句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我相信改我的那份稿子比他自己写还要费力得多。可惜稿子没有来得及发表就由于战争的原因遗失了,那份修改稿如能保存到今天,倒是十分好的纪念品。事过境迁,稿子如何写的和如何改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共有72匹马和多数是年岁较大的个体。
1935年,裴文中先生到法国去留学,卞美年先生又忙于其它工作,周口店的发掘即由我来主持,从此我和德日进神父间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每当周口店发掘期间,他总得到周口店去几趟指导工作。他一个人去的时候,总是从北京乘火车去,到琉璃河车站下车,然后改骑小毛驴走15公里的乡村小路到周口店。在去周口店之前,多半是由新生代研究室秘书高韩丽娥女士预先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到时我派人到琉璃河去接他。当时,在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相当艰苦,不但吃不好,住不好,行路也难,因为许许多多地方都不通火车或汽车,只能骑小毛驴或骡子代步,当然有时也能坐马车。他在华北旅行过很多地方,学会了骑驴或骡的本领,也很懂得牲口的脾气,随着他那“嗒——’、“驾——、“唷——”的吆喝声,那些牲口满听他的使唤。

他吃苦耐劳的美德很感动我。他每到周口店时和我在一起吃中国饭菜,什么都吃,从来不挑拣。有一次我和他从周日店返回北京,到琉璃河之后,才知道南来的车已经过去,只好等晚上那趟车了。傍晚,我们的肚子都有点儿饿,即邀他到火车站后边的小饭铺去吃晚餐。琉璃河是个小车站,虽然有二、三家小饭铺,但都既陋又脏,但他却吃得很香。我们吃完之后,他从桌于下面捡起一个死“灶马”(蟋蟀的一种,呈淡黄色,天气寒冷时常在炉灶旁跳来跳去),说是从他饭碗里捡出来的,缺了几条腿,恐怕是被他吃掉了。他怕我吃不下饭去,才偷偷地把它扔到桌下了。
去年,我和一些同行们又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1923年德日进神父发掘过的地方。1923年5月德日进神父从巴黎来到天津,放下行装不久,即和桑志华联袂北上,开始了他们的鄂尔多斯之行。他们的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狼山东麓,然后折向西南,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然后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银川市东南的横城,然后到达灵武县的水洞沟。当水洞沟的工作结束后才东去到鄂尔多斯。
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五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是为了东西来在旅客设立的。小店至多只能住四、五个人,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那里发掘的时候,据说是住在东口里,西间是张三夫妇居住,中间一间是厨房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过外国来客,面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惹起很大注意。直至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已亡故,但人们一提起这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是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和牛奶了。这座小小店房,现在虽然只保存下一点残迹,但对我的教育却很大,我也常常用这张照片教育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说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该有多么高贵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对我们年青一代,以至对整个的中国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过去都称呼他为德神父,现在我还依然这样称呼他。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周口店还留有少数人发掘第4地点,后来战争愈来愈紧,才完全停了工,只留下三人看守山场。1938年5月中旬的一天,有一位周口店的村民忽然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来找我,说:“看山的赵万华、董仲元和肖元昌三人被日军绑走,酷刑审讯,指为‘抗日便衣队’,于5月11日和其他三十余名“罪犯”押到房山县城西门外用刺刀挑腹杀害。”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兵马司中国地质调查所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给德神父,他当时正打英文稿件。他听到了这一噩耗,顿时嘴唇颤动,两眼直瞪着我,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地站起身来为死者默哀祈祷,随后一声不响地慢步走出他的房间。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我打算到大后方中国地质调查所去,到了南京正赶上珍珠港事件发生,海路不通,我又返回北京。这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已被日军占领,大家就散了伙。又过了两年,我和裴文中先生到东交民巷地质生物研究所去看望德神父。我们在他的宿舍里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久,从战争、工作一直谈到生活。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之所以记得日期,是因为当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当年的出版物——《化石人类》,上面写有“赠给贾先生,作为良好纪念”,下面有他的签名。虽然他没有写明日期,我却在他的签名之下写了“1943年12月20日”。此后虽然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但他的高大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写这篇纪念他诞生100周年文字的时候,勾引出我许多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我当时很淘气,在娄公楼和他同屋工作,每当休息的时候,我总是不愿绕远走门口,而经常从窗户跳出去。德神父一看开窗户,只好抿嘴笑笑,摇摇头。
作者:贾兰坡,原刊于《化石》1982年01期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
